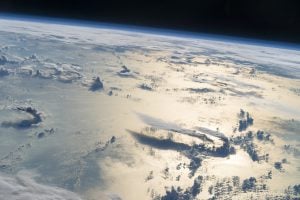短短十年之间,国际社会对中国环保成绩的看法经历了巨大的转折。曾经,中国是一些人眼中破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坏小孩”。而如今,中国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依旧高扬环境多边主义承诺的立场赢得了很多赞誉,被视为全球环境领域的领军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几年之内成功遏制城市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环保行动被誉为在国家层面对环境危机进行有效干预的典范。

在最近出版的《中国走向绿色》(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 (Polity, 2020))一书中,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李逸飞与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上面这种流行的看法进行了剖析。在对“煤改气”清洁供暖、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新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案例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本书的两位作者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强制力的环保模式的特征。他们认为,透过雷厉风行的环保政策,人们需要看到它背后可能存在的执行问题以及对实现长期环境可持续性的社会基础的影响。
最近,两位作者与中外对话进行了视频交流,讨论了他们的新书以及在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中世界应如何看待中国的环保新模式。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您曾经仔细考察过上海市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并将其作为“强制环保主义”的一个鲜活的例子。那么您从中发现了什么?
李逸飞(以下简称“李”):垃圾分类是一项触及所有上海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大政策。我们在这本书中介绍了这项政策的几个特征。首先,这项政策非常具有约束性。居民们必须每天定时定点倾倒垃圾,若在其他时间段倾倒垃圾严格来说都是违法的。社区还配备了专门的监督员,他们有权对那些未能正确进行垃圾分类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或罚款。这些政策设置都显示了其强大的“控制力”,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政策实施之前公众教育和垃圾分类意识的相对缺失。第二个特点就是执行中的随意性。我们一方面看到某些社区任意对居民倾倒垃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严厉的约束,而另一些社区的管理却相对松懈。
中:在上海之前,中国已经在部分城市开展了近二十年的自愿垃圾分类试点,但收效甚微。因此许多人认为,一定的强制措施是需要的。台北和东京著名的垃圾分类体系同样设置了垃圾倾倒的时间限制。那么,在环境政策中,什么程度的强制才是合理的?如何划分这个界限?
夏竹丽(以下简称“夏”):正如提出“公地悲剧”概念的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在环境政策中,我们需要的是“得到共同认可的强制”(mutually agreed coercion)。强制能够行得通的前提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就上海而言,强制垃圾分类的实施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是一件便于管理的好事,但未必考虑了公众的认可或者是让他们参与前期讨论。这就是我们新书中的论点:有时政府做出的环境决策意图是好的,但公众参与环节却是缺失的。正是由于缺少了公众的参与,这些“善意的”环境政策很可能结出不那么好的果实。
中:您认为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实现“共同认可的强制”?
夏:在许多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都必须征求公众意见和进行公共咨询,尽管许多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项工具。在中国,由于民间受到的较多限制,社会为国家建言献策的空间较小。但需要意识到的是,“群众路线”从延安时期以来就是非常著名的“中国特色”,群众的高度参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中国不应轻易丢掉这一传统。
李:要想达成共同认可的强制,我们并不需要去照搬别国的经验。政治协商是一项写入中国宪法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舶来品。我们在书中试图强调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全面唤醒这个中国已有的系统,并将其全面融入中国的环境决策,而且还要将它摆在首要位置上。
中: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规约”将环境政策转化为明确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党和政府的现代环境治理指导方针详尽地规定了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责任。这算是一种前进的方向吗?
李:这套做法具有很好的潜力,但如果参与制订规则的只有国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设计一套堪称完美的治理体系,并且对每个参与方进行严密的分工,以便他们彼此进行无缝合作。但是,如果这套机制无法与公众建立某种深层次的连接,或者公众无法参与到这个“完美”系统的设计中去,那么这个设计也就失去意义了。我们可以持续对系统设计进行完善,但它只有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夏:另一个问题在于,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确定责任分工的做法都给人一种技术治国的感觉。我们在书中就曾指出,目前有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趋势,也就是说将所有环境目标都量化处理。因此,执行政策的官员要想获得上级的好评就必须非常重视这些数字,以至于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的现象。
中:当提到强制性环境政策时,人们常常还会想到市场化解决方案这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也一直在尝试碳交易等市场机制。您在分析“中国式”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元素的?
李:市场机制不是我们这本书分析的核心内容。相反,这本书强调了通过强制手段治理环境给人带来的各种影响,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显然,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以及生态补偿等市场化机制对社会弱势群体并不敏感。这些机制追求的是整体效用最大化,并常常以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注意力转移到市场化机制实际上是让这些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生计面临更大的风险。
我认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会带来环境效益。全球很多地方都对碳交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能够证明这项机制可以切实减少排放的证据仍然很少。相反,这种机制似乎只是将碳排放配额重新进行了分配,将排放负担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公司,或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中:我们再以上海为例,建立废弃物回收价格机制是否会比当前的强制性制度更好?如您所说,这又将如何影响弱势群体?
李:美国许多州都颁布了瓶罐类废弃物的回收押金政策,通过经济措施鼓励回收。这项政策要求消费者在购买特定商品时预先支付回收成本。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这基本上就是要求他们掏出更多钱。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累退税”(regressive taxes),它在税率上对社会上的每个公民都“一视同仁”。显然,这个固定比例对最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
我要补充的是,在去年上海实行强制性垃圾分类之前,当地其实不是没有废品分类回收的存在。大量通过农民工等群体完成的垃圾分类回收早在政府强制干预之前就已经运行多年。他们骑着平板三轮车在城市大街小巷中来回穿梭,回收变卖废纸板和瓶瓶罐罐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官方的突然介入基本上就等于让这个从经济角度来说最愿意参与回收的群体一下子失去了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
中: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等科学家曾经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 “穷尽一切可能选项”。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对环保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挑剔。对此您怎么看?
夏:气候危机和其他环境危机确实都非常紧迫,我们的确需要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但我们也需要谨慎行事,看清环保举措背后的一些后果和问题。我们这本书是要敦促所有人睁大眼睛前进。我们当然赞赏中国为解决全球环境危机所做的贡献。但是,我们还需要确保人民的参与、最大程度地提高决策透明度、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我们也应该避免具有良好初衷的环保政策被扭曲。
李: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我们需要争取一切能够获得的帮助来应对环境挑战。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来说,现在是一个我们需要倾尽全力的时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的行政力量来保护环境,需要给予民间社会,比如环保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科学家和律师们参与的机会。应该积极鼓励他们发声,这样我们才能汇集所有力量应对危机,而不是仅仅依靠国家这双最强大的“手”。
翻译:Estelle